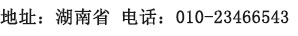侗族是我国对建筑艺术有着较高追求的民族之一。黔东南是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区——湘黔桂交界地区的一部分。嘉庆年间,贵州榕江、广西三江等地造船工匠已能造出载重2~3吨的木船,往来于榕江、柳州之间。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除农村的小集市外,一些集镇和县城,如王寨(今锦屏县城)以及古州等地,已形成较大规模的市场,清水江也逐渐成为全国较大的木材集散地。肇兴鼓楼杨代富摄明清以后,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多,贵州黔东南侗族聚居区的建筑形式逐渐发展出两种差异较大的体系。一是今清水江水系的天柱、锦屏,阳河水系的玉屏、岑巩、镇远,都柳江水系的榕江等地区,因水运发达而和外界有密切的商贸往来,建筑形式受江西、湖南、广西建筑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与干阑式建筑大不相同的变化。建筑使用砖墙围护、平面呈现合院布局、木雕装饰及墙体彩绘精美是比较明显的标志。二是在靠近广西、湖南的侗族聚居区,受到外来先进建筑技术的影响,木构建造技艺越来越成熟,出现了大量造型优美,结构各异的鼓楼、风雨桥,展现出侗族与众不同的建筑特征与民族性格。从江县增冲鼓楼王绍帅摄鼓楼是中国民族建筑的奇葩,而贵州侗族人民的鼓楼建造技术却又冠于广西和湖南。年落成的“从江鼓楼”,高46.8米,共29重檐,是中国迄今为止最高的侗族木结构鼓楼,比此前最高的榕江车江鼓楼整整高了10米。黎平述洞鼓楼,用直冲楼顶的中心柱作为整座建筑承重结构的枢纽,底层围之以九根檐柱,平面呈方形,以上各层及楼冠部分均以穿枋与层层瓜柱进行连接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整体。中心柱又称都柱,是中国唐代以前才有的木结构形式,除日本尚有遗构外,中国其他地方已无实例,独柱鼓楼堪称孤例。江县增冲鼓楼王绍帅摄增冲鼓楼是目前已知的、现存的最早侗族鼓楼,位于从江县往洞乡增冲村。根据侗族“先建楼后立碑”的习惯,从增冲村现存的《万古传名》碑推断,增冲鼓楼始建晚至清康熙十一年(年)。鼓楼建成之后的三百年间,曾多次维修,但主体结构至今没有大的损坏和更换,在潮湿多雨的贵州地区十分不易。鼓楼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双楼冠塔状建筑,通高21.5米,有落地柱十二根,其中金柱四根,檐柱八根,中心放射环形分布。楼身上置两层八角攒尖宝顶,俗称“楼冠”。楼冠下部及中部均施五层如意斗栱,叠加于三十二个坐斗之上。这两层斗栱侗语称“干梗”,孔格交错,远望如蜂巢一般。檐角高翘,为鼓楼的顶端,宝顶上用圆珠陶瓷,依大小顺序串联一起,形成尖顶直指云霄。鼓楼楼身各层翘角泥塑人物鸟兽,檐板彩绘人物、花草、图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鼓楼南门门楣上有“二龙戏珠”灰塑,挂“万里和风”木匾,该匾是榕江车江三宝侗寨于“道光五年”所赠,也足证该楼历史之悠久。从江县风雨桥王绍帅摄风雨桥在中国南方普遍分布,但悬臂叠梁结构形式的风雨桥却是侗族工匠的一大创造。在跨度较大或为了追求美观效果时,侗族风雨桥往往采用悬臂式结构。悬臂梁有单向伸臂和双向伸臂两种形式。单向伸臂以桥端岸壁为基点,用若干层木梁,每层递出伸臂,逐渐向桥心靠拢。每层悬臂一般5~8根圆木,每两层悬臂木梁之间用木隔梁隔开。木隔梁间距2~3米,既起到分散荷载的作用,又让悬臂梁形成一个稳固的结构体系。为了增加稳固性,每层单向悬臂梁尾部均用石块等材料进行填压,这样就使悬臂根部形成了一个柔性的木架支座。双向悬臂做法与单向悬臂相似,它是在河心桥墩顶叠架木梁向两边平衡地伸出,与相邻桥墩的悬臂结构共同组成受力体系,并在两个悬臂之上再用圆木铺设桥梁。这样处理之后,就大量增加了桥梁的跨度。地坪风雨桥贵州黔图库供图地坪风雨桥造型优美,结构合理,是侗族风雨桥的杰出代表。该桥位于黎平县地坪乡的南江河上,始建于清光绪八年(年),多次遭受水火之灾。年毁于火,年重建。年又毁于水,幸得当地群众奋力抢救,桥梁的大部分构件被打捞上岸。年8月,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风雨桥按照原来的实测图进行修复。桥全长57.61米,宽5.2米,桥面距正常水位约10.75米。桥上建三座桥楼,中楼为五重檐四角攒尖顶塔形建筑,高10.2米,两端桥楼为三重檐四角歇山顶,高5.8米,桥顶各檐翼角高翘,白灰瓦头和封檐板,桥正脊上塑鸳鸯、鸾凤和二龙戏珠。桥两端入口柱壁上共有楹联三副。廊两侧设长凳供行人休息、避雨、乘凉、会友、迎宾送客和观赏风景。廊壁绘有侗族妇女纺纱、织布、刺绣、踩歌堂以及斗牛和历史人物等图画。天花彩绘龙凤、白鹤、犀牛等,情景逼真,形象生动。地坪风雨桥木梁结构为悬臂式,为了增加跨度,近十米高的桥墩之上设托架逐层向外悬挑形成桥台。桥台用五层圆木和方木,以纵横叠加方式构成,呈倒金字塔状。桥台之上为两层木梁,两层木梁之间用圆木横向隔开,木梁与木梁之间用横枋榫连。通过榫卯连接,桥墩、桥台及木梁形成了桥梁的承重结构,在结构科学尚未开化的年代,能够建造如此大跨度的木构建筑实属不易。肇兴侗寨鼓楼花桥美景杨代富摄侗族建筑工匠的确是值得尊重的中国传统木构建筑技术的传承人。他们从不曾忘记坚守,但也从未墨守成规。他们总是醉心于木构建筑的不断更新和变革,将人类“更高建筑”“更大跨度”的追求融入鼓楼、风雨桥的建造中,使侗族鼓楼、风雨桥不仅代表着侗族建筑技术的最高水平,而且也是我国木结构建筑技术的典型代表。文章内容有删减全文请见《乡村地理》年春季刊或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