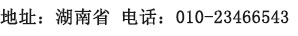终于失踪多年的柳江玉桥亭古碑有下落了:
李世宗老师著的《柳江古镇轶事趣闻》一书中的文章“闲话玉桥”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桥头亭上耸立着一排高高矮矮的石碑:明文林郎御史张鹏故里、大清特授湖北知府带江先生张柱故里、大清贵州巡抚枢元曾文诚公故里、明义士余飞先生故里、乡贤何兰亭先生故里……另外还有一块小石碑置于桥亭石坎之下,被荒草淹没,很少人看见,那碑上刻有《修桥记》。大意是说明末清初这里居住着柳姓、姜姓和俞姓三大家族。柳姓和姜姓共同修建街道,俞姓负责修桥。修好后,街就名柳姜,桥名俞桥。随着岁月变迁,后来柳姜改名为柳江,俞桥改名为玉桥。可惜这块碑和桥头上所有的碑都不知去向,难以找到了。”
从上面描述可以看出,李世宗老师亲眼看见过俞桥亭上的那些石碑,后来不知去向。至少在他出书的年5月,李老师都不知道石碑的去向。
碑上的人物皆是柳江历史文化名人,很多年来为柳江这片乡士传递着正能量的人。石碑是何时不知去向的,李老师没有交代。其实,凡是关心柳江的老人,都会为玉桥亭上的这些石碑的不知所踪感到惋惜。
八十六岁高龄的尹道新教授好不容易回柳江来了,他回来四处奔走,就是为找寻古迹的。他先去找“天子门生,门生天子”的匾,无果。又去曾璧光小时候住过的居所照像的同时在铺地的石板中四处寻找,据说他过去在这里见过,柳江名医谢斐然先生纪念碑的殘片也无果。
接下来他又去问喻桥头那几家饮食店,亲自去楼下查看了几个石缸,最后终于访问到了原王槐征家,槐荫山房门前大石缸。据尹教授说,王槐徴此人饱读诗书,在乐山嘉定联中与郭沫若是同学,也写得一手好字,那石缸上就是他写的智者乐三个一平方尺以上的大字,此三字源于孔子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他将智者乐三字放在水缸上,不仅很有内涵,而且字也写得很美,加上石刻技艺特好之外,也刻的特别深,欣赏起来妙趣横生,耐人寻味,可以说这是一件人文与艺朮兼具,值得展示于柳江的,堪与曾家院两泰平缸相比美的古董。
终于落实了,此缸现存于花溪一位教师家义里,尹教授记下了他的电话这才放心了。
他到原来的道子坝看柳江古镇书画院,遇关门,随后要了一碗冰粉,在树荫下慢饮,尹教授是老柳江人,认识他的人特别多,其中一个扫地的妇女热情地招呼尹教授,得知他是要去看书画院的时候,便主动去叫人帮他开门,尹教授如愿以偿地参观了书画院。
离开时,那个扫地妇女也来热情地送他,叫他在柳江多耍耍。尹教授顺便问她:“你在这里扫地,知道玉桥的几通碑不?”那个扫地的妇女说:“知道,就在我家,我的公公爹拿去做猪圈去了。”尹教授问得她公公爹名叫罗光伟,已去世几年了。罗光伟的儿子名叫罗裕祥,现居住在红星三组。
尹教授得到此信息,可高兴了。他说:这真是个奇缘,如果不是罗家事先移走,这几砍历史文物肯定难逃文化大革命那一关。在那种风潮中,有几千修水电的往在柳江,如果有任何一个小子,只要随意拾一块石头敲几下子,这些石碑还能存在至今吗?应该感恩于罗光伟的保护,给他追记功德。我有一位西师同学谢富政,是西南交大教授,他在一本画册的序言中就写得有:文风扑面儒雅的柳江,这种说法有什么物证呢?除了碑林的现代碑而外,这几块往昔遗存下来的沧桑感就很深沈和厚重,这些更能彰显柳江历史文脉的古碑,因而也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了。
得知玉桥亭上的碑的下落后,笔者亲自到罗裕祥家中去考察,还是扫地的那个阿姨接待了我,她把我带到堪有名人碑的毛坑处去看了看,由于装满了粪,无法看清。阿姨说,只有等以后把粪舀干后才看得到。以前,王永寿和张明林去拓过那些碑。
当我把得知石碑的消息告诉柳惠均老师时,柳老师说:原来修柳江碑林时,汪开武就去暗访到了,知道玉桥的几通碑在罗光伟家中。柳老师还关切地问石碑还还得原不?我想:装了满满的一坑粪,估计那碑没有损坏。但愿文物部门引起重视,早日让石碑重见天日,继续为柳江人和游客传递正能量,发挥其应有的历史文化价值。
文章作者:姜纯秀图文编辑:唐从祥
原文标题《发现洪雅之柳江玉桥亭古碑寻找记》
转载请注明出处!
↓↓↓点击阅读原文,参与洪雅本地事件评论。
爱我请给我好看!预览时标签不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