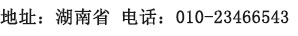文明因水而兴,在世界文明的起源中,非洲尼罗河、西亚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中南亚的印度河与恒河、东亚的黄河和与长江等等,这些河谷对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乌江腾龙峡全景思南县文旅局供图
作为贵州最大的流域,乌江绵延数百里,一路逶迤向前,润泽黔中大地,被视为贵州的母亲河。这条河流到底孕育、见证了哪些黔地文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的单位对乌江流域展开一系列的考古工作,逐步解开这一流域的文明密码。
“双洞”文化里的秘密
20世纪70年代,以贵州省博物馆为主的考古单位组织发掘了硝灰洞古人类遗址、穿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两处古人类遗址的考古成果证明了乌江流域自古就是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
在乌江思南河段,可见拓碑“黔中砥柱”,这是历史上对贵州教育有重大功绩的田秋所提。思南县文旅局供图
硝灰洞古人类遗址位于贵州省水城县西北25公里,即乌江上游公里河段上,这里离乌江源头70多公里。遗址的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考古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硝灰洞是从前有人在洞内熬硝而得名,洞内的文化层中出土古人类牙齿化石,经过研究表明,这里的古人类比“北京人”进步,比“柳江人”原始。另外,通过考古还发现东剑齿象、野牛、野羊、野猪、野鹿等哺乳动物化石,出土石器、计石锤、石片等等。这些石器的加工方法也很有特点,石片用锤击打制,或用锐棱硬击打制,也是全国所有旧石器遗址中独一无二的加工方法,代表了一种新型区域性文化。另外,硝灰洞遗址内发现多处用火遗迹,发现含有多种颜色的灰烬,这也是我国华南地区古人类用火年代较早、较丰富的可靠证据。
穿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乌江中上游,贵州省普定县城西5公里的新寨孤山上,因洞口南北对穿而得名。这里出土石锤、石砧(捶或砸东西时垫在底下的器具)、石片、石核5千余件;骨针、骨锥、骨铲、骨叉6百余件。还出土了竹鼠、豪猪、牛、鹿、虎、熊、猕猴、犀牛等20多种哺乳动物及人类化石2万余件。其中有一具比较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经研究得出这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女性。另外,遗址还有烧石、烧骨、烧屑、灰烬等多处用火遗迹。经考古学家认定,穿洞遗址的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一万五千年。
一江融巴蜀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提到:在乌江流域多次开展考古工作,发现了众多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古代墓葬、古建筑、古遗址、古窑址、古代文化遗存等。记者梳理这些考古发现,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再到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一系列的考古成果证明了乌江流域独立展示了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轨迹。
有意思的是,众多遗址发掘中,都可发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乌江流域所发现的文化遗存都与峡江地区的巴蜀文化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反映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起,通过乌江流域,峡江地区古文化与黔东北地区就有了交流。
古纤道 思南县文旅局供图
比如处于乌江和小河交汇处难免一级台地上的坝上小河口遗址,隶属沿河县和平镇,这里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器物与成都十二桥文化出土器物近似,应属于巴蜀文化在贵州境内传播的重要地点,也是乌江流域目前发现、发掘的巴蜀文化在贵州境内分布的最远地点。另外,老坡底遗址出土器物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遗址有较多相似,可能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顺乌江传播的结果。黑獭遗址群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与乌江下游及长江三峡地区遗址基本相同,应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可作为长江流域古文化向乌江流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反映。
藏在河谷里的时间胶囊
记者梳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乌江博物馆名誉馆长汪育江老先生编著的《乌江流域考察记》等资料发现,乌江流域的众多考古成果展示出地域性强、自身文化特点深厚,但又具有从东西南北不同方向而来的文化融汇特点。可见,乌江流域是探讨古代民族文化交流与碰撞的重要地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贵州自古就是多民族融汇,文化丰富多彩,如今贵州主打的文化旅游品牌“多彩贵州”,可谓自古如此,名副其实。
《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提到:地处乌江上游鸭甸河与鸭池河汇流处,贵州清镇、黔西、织金三县交界河谷地带的化屋基苗寨,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少数民族石板墓;沿河县的洪渡汉窑址群是目前贵州清理数量最多、结构最清楚的汉代窑址,对了解汉窑的生产程序和建造方法等具有重要价值。通过窑内出土的汉砖汉瓦与乌江流域汉墓使用的汉砖情况的对比,可以分析这些窑生产的产品销售范围,有助于研究乌江流域与周围地区的文化交流。与此同时,洪渡周边的汉代遗存在探讨汉文化进入贵州的路线上具有重要地位;《乌江流域考察记》中记载,思南县城北15公里的桶井乌江渡口的百丈悬崖的彭家洞取出一具洞棺,尸体棺本衣物基本完好,从服饰看,是一个明时的二品官。作为土著民族施行悬棺、崖棺、洞棺的葬俗并不奇怪,但作为明代朝廷的二品官施行这种葬俗就值得研究了,或许与民族习俗的融合有些关联。
乌江沿岸有不少历代名人墓葬,比如蜀汉大将庞统独生子庞宏墓、唐代名相长孙无忌墓、宋田祐恭墓、宋杨粲墓等等。这些名人墓葬背后的故事,名人生前的功绩,都或多或少与贵州的文化发展有些关联。比如明田秋墓,他生前的故事就值得一说:田秋的政绩以在京做谏官为最有名气,明永乐年间,贵州建省后,年间没有设乡试,贵州的读书人要考举人都得到千里之外的昆明应试。那时,除少数富家子弟外,很多贫寒之士无能为力,因此埋没不少人才。当时田秋力主贵州开设乡试,并以亲身赴昆明应试所受的路遥之苦向嘉靖皇帝上了奏折,后得到嘉靖皇帝赞许,在贵州首次开科。《贵州名贤传》中的《田秋传》中对他的这一政绩有所记录:“从此贵州人才四起,直追中原。若论起扶持贵州文化的功劳来,真要推田秋做首功呢!”
乌江边的文化故事数不胜数,见证的贵州文化发展何其厚重。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用考古当“钥匙”,或许,将来还有更多的乌江流域文明密码等待着我们打开“时光之门”去探索、去发掘。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谢予谦
编辑聂娜王亚玲
编审查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