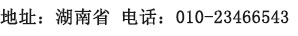《滋根三十年人物故事》编者按:
年是滋根创立的第三十个里程碑,三十年的风雨,期间我们遇到了很多人,他们性格鲜明,艰苦卓绝,无数色彩斑斓的故事便在这条长河里发生。我们相信,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故事。我们将通过系列人物故事向您展现这风雨兼程的三十年。
为有着多名学生、服务多村民的乡村学校不受撤并而努力;龙校长动员村里的乡土艺人给学生上民族文化课,有寨子里的老人、有教苗歌的妇女;积极奔走向社会各界寻求资源,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助学支持,为学校引入文体图书器材、常用医药,修建食堂、改善学生伙食和寄宿生活条件;他还带领老师学习上网、开通微博,让大山深处的苗寨学校与外界保持连通。
一所好的乡村学校,不仅要关心学生点滴,还需连接村寨,也要连接社会,整合不同的资源,来为村寨、村民、学生服务。龙安吉校长毫无疑问是一个能够坚持到底、服务家乡的优秀乡村学校校长和教师。
(年首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奖”推荐词)
图片|杨建
人物简介:
龙安吉,男,生于年,18岁凯里学院大专毕业就参加工作,在自己的家乡高扒收拾牛圈办起了学校,人称“牛圈校长”,他腾出家中房间无偿给远路学生居住,还捐出自家木材建校舍,在教师岗位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他撬动多方力量,保住了学校,他还在为本民族的文化能够得以传承而不懈努力。年获“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奖”,年入围“马云乡村教师奖”。三十多来,龙安吉一直坚持不让一个山里娃辍学。
高扒,全镇唯一的苗族村子,位于风景秀丽的山顶。据说很久以前这里叫“乌登”,因为苗族没有文字,这里的地名说得出来却写不出来。解放后明确行政区划,乌登没有人在场,考虑这里人们住得高,又是悬崖上,“悬崖”的侗话读“扒”,于是这里就被写成“高扒”,意思是“高处的悬崖”。
难忘的牛圈教室
八十年代前,全村没一人识字,连一封信都要请外地人念!村里有史以来没学校,全村苗族孩子全当放牛娃,年我刚念完书回到家,主动找到村长召集村民大会,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须掌握文化和科学知识,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当文盲。村长说:“小龙,我们村处在深山里,一没学校,二不通路,城里的秀才请不来;要是你能当我们村第一任老师那多好啊,我将代表全村人民感谢你”。当时我很想到城里去发展,但村里有那么多孩子没老师上课,耽误一届学生影响的是一代人的文化素质,就决定留下来教学生。当时村里的房产只有唯一的一间集体建的牛圈,就以牛圈当教室吧!路远的学生就住在我家,多的时候有六十多人。从此,高扒村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所小学。
山里的放牛娃第一次听到报名上学,第一届有13名学生报到。没有桌椅,号召学生从自家带来高矮不齐的桌椅来用,架板子当课桌,石头当凳子;带学生清理牛圈教室里的牛粪,打扫卫生,学生乐得像猴子游花果山一样蹦来跳去。斯是陋室,师生们乐在学习中。开始教学生懂礼貌,习执笔,学识字。有的家长也跑来听课,跟自己的孩子一起上课。最早只有男生来上学,后来经过动员宣传和国家政策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女孩走进这所学校。
学生来了,住宿是个问题,高扒村分为10个自然寨,最远的六组距学校有8公里,学校没宿舍怎么办?为解决住校生的困境,我就跟家人商量腾出自己家的三间木房给学生住,直到新校舍建起孩子们才搬进漂亮的学校。
高扒小学的老师们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教书育人的工作。教学器材奇缺,学校没有任何体育用具,体育课只能是做做操,跑跑步,跳跳舞。一副教学用的三角板和一块量角器,还是老师们自己用木板做成的。学校没有球场,只有正在新建的教学楼旁边有块平地。平地边上,虽然也立着一个篮球架,但地方实在太小了,还没有普通标准球场的一半大。别说是没有球,即便是有球,球也很容易就掉到远远的山脚下。学校也没有厕所,原来破旧的厕所,经过今年年初的那一场大雪,已经完全不能再继续使用了。(胡志鸿,3年)
我们在阴暗潮湿的牛圈里度过了十三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在牛圈里读书考取大学的学生有9个,龙再忠,贵州大学;龙见花,海南大学;龙敏,西北大学……他们的名字我一个个记得真切。最难忘牛圈上课的岁月。
牛圈学校由于时间较久已成了危房,容纳不下这么多学生,当时国家财政困难没钱投入,为改变办学条件,我们想办法自力更生。我自己带头先捐出我家20个立方的杉木,加上全村捐献的10多方,在群众投工投劳下从建起了高扒全村最漂亮的木房,高扒小学从此告别了以牛圈当教室的岁月。
年第一次接触滋根,并从此开始成为了滋根的一名义工,与滋根的交情一晃二十余年。当时,高扒还不是完小。因为教育局的推荐,滋根通过女童助学项目来到高扒“牛圈学校”,这里没有一名女孩儿曾经上过学、识过字,滋根当时要做的,就是支持当地贫苦的女孩上学。
滋根是1年秋季开始资助这所学校的,每学期资助30个贫困女儿童读书。在接受资助以前,学校的女生入学人数很少,每学期平均只有2~3人,被人称为“和尚小学”。滋根的资助极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现在,在学校的个学生中,女童的人数达到67人,超过了男学生的人数。2年入学,今年读二年级的那个班,全班28人中竟然有20个是女学生。这倒不是高扒群众已经从“重男轻女”变成了“重女轻男”,而是那些过去没有能够读书的超龄女童,现在到学校里去补织那些逝去了的梦。(胡志鸿,3年)
坦白地讲,滋根工作人员来到高扒,我觉得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够支持女童上学,帮助改善村寨重男轻女的现状,为村寨带来切实地帮助。一直到今天,滋根仍在支持高扒村内女童、学生上学,与此同时滋根也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帮助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推动环保节柴灶、支持民族文化传承和开展教师培训等。
多年的接触相处下来,我被滋根的理念影响打动,尤其在思想上,向滋根学习不求名利做贡献,“哪里有困难就要到哪里”。滋根所做的事即是“爱心正能量,真情满人间。”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解决急需的问题。
在学校,我们一方面抓好汉语教学,一方面在中国滋根等公益组织的长期支持下,为抢救和传承我们本民族的灿烂文化,坚持乡土文化进课堂,让学生在校园里学习苗族古乐器(芦笙、飘琴、铜笛),还教学生歌舞传说等。
文化是我们的根
随着教学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学校教孩写字、学习现代知识,那么,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怎么办?孩子们知道我们生养于此的一切是怎么来的吗?比如我们的历史、歌谣、舞蹈、服饰、建筑、信仰、农业生产,乃至于风俗、生活习惯等。从课本、现实生活和其他媒介看到这么多自己没有的“花花绿绿”,他们还能够自信吗?
我们属于贵州都柳江苗族支系,苗族没有文字,祖先的文化历史都以古歌、故事、乐器弹唱等形式进行传承,古歌叙述祖先迁徙的艰苦历程、庆祝五谷丰收、喜迎重大节日、举行宗教仪式、鼓舞战士出征等,涉及天文、地理、宗教、建筑、科学、气候等等,苗族古歌被称为“百科词典”,从我们的祖先一代代传唱至今。但是,现在会的人越来越少,如果失去这一切,我们还称其为“我们”吗?祖先积淀几千年五彩缤纷的民族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消失。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中,我也观察了解到:
农村孩子1至4岁在父母身边还学不完本民族母语,从5岁开始离开父母进入学校强化学习汉语言文字一直读到大学,她们离开家乡,离开本土文化的洗淘,在外读书、工作、打工到老,造成了乡土文化严重失传。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延伸,每天有上百个传统村庄在消失;撤并学校集中办学,师生撤走;青壮年打工,村寨精英和领头人流入城市淘金,村庄只剩留守老人,村寨文化和农耕文明呈现荒凉景象。
校教育与民族文化合一办学
年,我教音乐课时,原计划教的是校园儿歌,全班学生一致要求教唱苗歌。从那一节课开始,乡土文化进课堂轰动了全村,在学校还能学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很多家长就支持送女童上学,女生逐年增多,直至适龄女童全部入学。
学校利用音乐课和课外开设有苗歌、芦笙、铜笛、瓢琴四个兴趣课程,作为常设课程一直办到现在。我们动员村里的歌师,包括女歌师来学校教授;也支持学生参与村寨的文化活动。
学校把乡土文化和国家主流课程合一推广,学生接受了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贴近实际的乡土文化的启蒙,形成了乡土和民族的认同,学生心中有根,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家”,而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根”也保留下来了。民族文化得到传承的同时,也成为我们学校独有的一张名片。